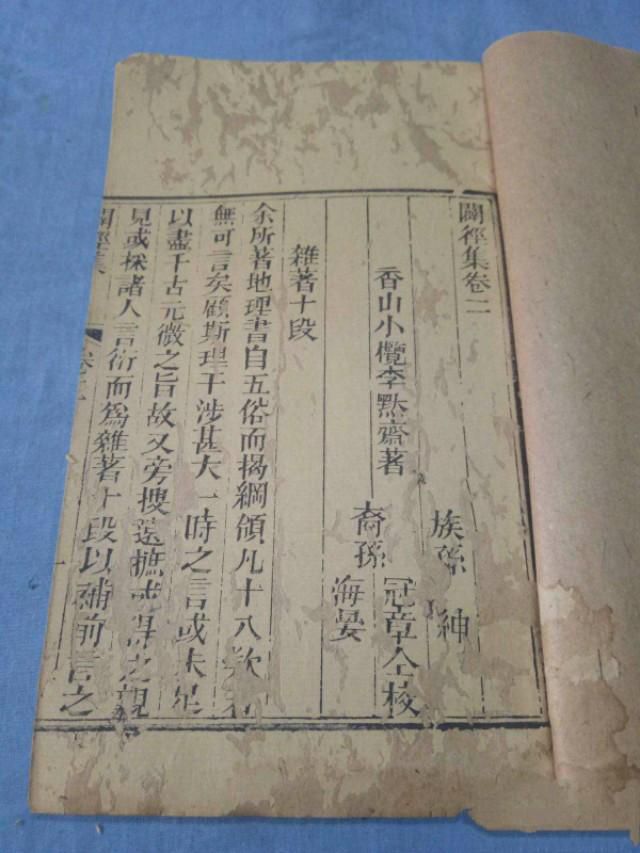文:楊士毅 教授|圖:編輯部
1968
年,我在建國中學念高一,那時開始對「算命」感到興趣與好奇。有時拿起父親在我出生時去找大稻埕命相家曾定里所批的八字(即紅色的命書)去「研究」,但只看懂總評中的部分詩句。
高二那年,我常和同學在下課後步行穿過植物園到中山堂附近搭車回家。但有時下課比較早,就去重慶南路逛書店。當時翻閱命相書的目的就是想了解自己的命書所隱藏的意義。但是,子平法的書實在很難懂,其至想找一張和自己的八字相同或非常類似的,都沒找到。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八字的排列組合太多了。
當時,也常對自己的掌紋去看手相的書。有的手相書很容易看懂,但有些採用陰陽五行與八卦的理論就看不懂了。
1971年,考完大學聯考。時間非常空閒,當時最大的樂趣還是到重慶南路去逛書店。由於高三國文老師上課常提到《易經》,再加上高二時,看算命書籍,每當碰到陰陽五行與八卦的術語時,就看不懂。因此,就想利用這個暑假去讀《易經》。但也因此鬧了一個笑話。
有一天,我獨自跑到一家專售《易經》等書的專業書店。告訴一位年紀相當大的店員說:「我要買《易經》。」他問我:「你要買那一本?」我聽不懂,就說:「《易經》不就是書名,而且只有一本。」他笑一笑,指著書店中整片書架說:「這些都是《易經》!」我一看嚇呆了!怎麼那麼多種「易經」,大概有幾千種吧!我就請他幫我推荐一本,他看我高中生的模樣,就介紹了一本「入門」的書。
回家後,我努力閱讀,也記了八卦的口訣。但是到後來才發現:單純的《易經》和卜卦雖有直接關聯,但和子平法與紫微斗數等算命方法只有間接關聯。單單唸《易經》,還是看不懂命相的書及自己的命書。
後來,我在大學念物理系、哲學碩士班及博士班時,都特別修了「易經」的學分。在1988年,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舉辦「中國哲學與懷德海」的比較哲學會議,我也發表了一篇〈《易經》與懷德海〉的論文(收錄於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東海哲研所主編的《中國哲學與懷德海》)。
聯考放榜,我考上中央大學物理系。畢竟成為像諾貝爾獎(Nobel Prize)得主楊震寧、李政道一樣傑出的物理學家一直是我初高中時代的夢想,可惜,命運的安排使我並未走向物理學家之旅。
大一時,我仍然繼續看手相學的書,但依然非常膚淺。當時的我,相當木訥。但大一下,卻發現幫別人看手相,很容易和別人交談。因此看相變成我大一、大二生活中的樂趣之一。雖然當時算的內容很浮泛,其至帶點吹牛的性質,但是,我發現大部分被算的人都蠻高興的,有些人還客氣的說:「算得蠻準的!」或「有點準!」
一直到數年後,我碰到數位手相面相的高手,才知道看手相面相是相當高難度的算命法,至少必須具備在黑暗中分辨出藍色與黑色的能力,而且最好以具體的人為例去學習,效果才會良好。單看書幾乎不易學到精髓。
其中有位高手由於是家傳的,並曾發誓不外傳。因此,我也不可能直接學習到。但是,有時和他一起去逛街時,他會說:「像這個人是屬於那類型的人,他是如何如何……。」
由於手相、面相的細紋與氣色往往隨著年齡的成長、事業的興衰以及婚姻的幸福與否,而改變,因此最難觀察的就是氣色與氣質變化。但是我曾遇到一位專家,他看一個人不到兩分鐘,就可猜出十個答案,大約可中六到八個,當然這是他最專長的;至於其他的預言就不是非常可靠了。
此外,說話的聲音也非常重要,我曾經遇到一位真正與世無爭、真正修行的隱居高僧願興師父,他的眼神與直覺迥異於常人,精通子平法、風水及麻衣相法,尤其重視「聲音」。1950年代,先總統蔣介石曾去拜訪過。在他九十多歲時,還曾去歐洲雲遊。
總之,手相、面相……等內麻衣相術不像紫微斗數或子平法在人一出生時,其命盤與八字就永遠固定。前者一直在變化中,無論我在麻衣相術的功力是多麼地膚淺,但是我的命相之旅確實始於手相、麻衣相術,並持續至今日。
1972年,由於中大物理系在二年級時,必須先修半年的《近代物理導論》;所以,接觸到了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論,它引起我對時空問題的研究興趣。結果發現哲學領域中的維也納學圈及邏輯經驗論的科學哲學,對這方面的討論非常多。當時的我開始迷上這方面的哲學。科學哲學經常喜歡用占星術、馬克思主義(Marxism)及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演化論為例來討論其是否科學、或偽科學、或前科學、或不科學。在本書中,我也由科哲的觀點,討論了命相學的科學性。
1973年,大三上,我又由科學哲學走向研究子平法、《易經》或卜卦。研究這類學問幾乎占去了大部分的閒暇時間。甚至在大三下,我還利用正課時間,專心研讀上述書籍。
也許是受過物理學、數學及地球物理中有關宇宙起源、星球誕生、地球內部的結構等科目中高度的抽象思考、邏輯推論、及想像力之訓練;因此,獨自閱讀這些書籍並不會感覺吃力,甚至常產生奇妙的心得。
那一年,我經常幫熟悉的同學或朋友用子平法算命及用《易經》原文去卜卦。記得有次補考前,還和郭烈銘、黃仕光、宣大衡等同學卜卦看會不會過關。記得當時卜的卦相並不是「大吉」,大約是「小凶」。結果,黃過了,我被當了。
由於經常卜卦,很自然地,《易經》六十四卦也跟著念了好幾次。卜卦、算命成了大三緊張生活的調劑品。
不過在大四時,我大三時的室友謝福淵告訴我,當年(指大三下)我有點陰陽怪氣。這也是學算命的人要注意的,相信讀者很容易觀察到有些算命者的氣質迥異於常人。算命工作者若要化解上述氣質,一定要培養出「達觀開朗」及「助人」的心境,並化掉幫人算命卜卦時所形成的壓力,同時言談儘量培養幽默感,並面帶輕鬆的微笑,更要把算命當作生活的樂趣與藝術。我想:當謝同學告訴我時,我大約已化解掉陰陽怪氣了。
大四上(1974年11月),我受臺大哲學系李明珠同學之託,幫她的同學算命。那時,我仍偏重子平法,而且覺得紫微斗數比較呆板。這是我第一次對完全沒碰過面的人算命,地點在臺大學生活動中心的會議室。當時圍觀的同學好多人。為了避免漏氣,我足足準備了一天的時間,並做了筆記、引用了一些哲學家的名言、在算了一個段落後,突然有人傳了一張紙條要我幫他算。由於已近中午;因此,就延到下禮拜一再算。
隔日禮拜天,雖然感冒、體力較衰弱。但我還是準備了半天的時間。就在星期一算完後,她說了一句話,令我終生難忘。她說:「謝謝你給我信心和勇氣。」(地點我還記得很清楚,是在臺大文學院的特二教室,現在歸文學院圖書館使用)。這句話使我對算命充滿了信心和勇氣,也使我日後只要有空閒,就義務幫有需要的人算命。我經常結合算命、現代科學知識、哲學、心理學與自己的社會經驗,努力使被算的有緣者產生信心與勇氣,甚至透過此去從事正規的心理輔導工作。
命相變成了我日後十多年,在研究哲學及教學之外,非常愉快的工作之一,因為,我確實從被算者充滿信心及愉悅的表情中,獲得了相當多的鼓勵。透過這些命相經驗,使我的人生之旅增添了許多豐碩的果實與絢麗的花朵。也因此寫成了幾本書如《命運與姻緣》、《命運與人生》及《愛.婚姻.家庭──差異.衝突與和諧》。所以,反過來,我必須感謝前述所有有緣者。
嚴格說來,要使人們充滿信心和勇氣並不是那麼簡單,尤其是要在短短的時間內。當然更不是只說些好話即可達成目的。它需要命學知識再配合當代的科學知識及豐富的社會與人生經驗及嚴謹的邏輯論證,以便提出解決疑難的方法,同時也必須善用種種中性語言與價值語言,才可產生良好的效果。
也許是命運及緣份的關係。1978年,我從陸戰隊退伍,隔一年,考上哲學研究所,我仍繼續鑽研與科學關係密切的哲學及《易經》,有時也幫人算命。
有一天我心血來潮,去拜訪一位朋友,碰巧遇到兩位命學高手,其中一位在幫我算命後,主動告訴我,他想出國前教我「飛星紫微斗數」。
就這樣子在他出國前數個禮拜,每天早上去他們家補習。他全然不看書地口授,時間很快地過去了。但由於他的傾力傳授,頓使我更深入體會以前所研究的子平法及粗淺的紫微斗數。
在他出國前夕,他送我一本書,同時期望我能寫這方面的書。
後來,另一位高手又主動教我斗數中另一學派的其他內容。
學算命若能遇到有緣的高手,主動傳授給你,而自己領悟力又好,則短短一個禮拜就比自己看多年的書有效多了。從此,我就以紫微斗數為主,子平法、手相、面相為輔,採取綜合算命的方式,義務幫人算命看相。
從上所述,可知:我之所以研究命相或幫人算命,主要在物理系時代,和我念哲學研究所並非直接關聯。換言之,哲學並不等同算命,也不是研究哲學的人就必須研究算命。但算命難免會連接到哲學,東西皆然。而西方科學家、哲學家熟悉占星術的專家也不少,如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丶刻卜勒(Johannes Kepler)、牛頓(Isaac Newton)等等。
算了三十多年,大約三百六十五行的人,都經歷過了。
在這二十多年中,雖然有許多人說我算得蠻準的,但我內心深處始終有種奇妙的感覺:你說算命很準,卻不像物理、數學那麼精確,而且差多了,可是你說它完全不準,卻又不盡然。「算命」既不是「迷信」或「無稽之談」;也不是察言觀色、依照被算者的心理及反應順手推舟而已。它的科學性介於科學與不科學之間的過渡領域;它的精確度,介於科學預測和宗教預言之間;它的神祕性也是介於上兩者之間。
此外,在我幫人算命的人生之旅中,附帶產生下列奇妙的感受:每逢我處於情緒(或命運)低潮時,大約被算者的命盤或八字也不是非常容易解釋。反之,在高潮時,則靈感大增,更能輕鬆地為他人解釋疑難。
更重要的是,許多被算者在算完後往往充滿了許多信心與希望。我曾經嘗試從心理學與哲學去合理解釋,但都失敗,因為命學還包含了一些心理學或哲學所不能解釋的神祕內容,雖然我喜歡在空閒時,運用各種知識與經驗幫人解答疑惑,但是在情緒低潮時,就很少幫人算命。
也許是道德感及教育使命感的影響,再加上多年的反省,使我覺得算命看相並不需要刻意去提倡,順其自然發展就好了。但是對有些喜歡算命看相、或對此感興趣與好奇者,抑或極端排斥者,我倒覺得有必要讓其以較正確的態度去了解何謂命相學、何謂命理哲學,或許更有益於人生與社會,乃著手寫有關命理哲學的書,但不是如何算命的書。其目的只是想説明命相學不是迷信,也不是精確如物理學。它是介於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模糊地帶,人們不需要太神化它、也不需要排斥它,或輕蔑它。就當它是個參考、是個生活的樂趣。當然若能使自己對未來更有信心與勇氣,或至少被算命後很快樂或解惑,那就非常有正面價值了。最後祝大家大運(十年為單位)、流年運勢亨通、日日是好日!